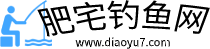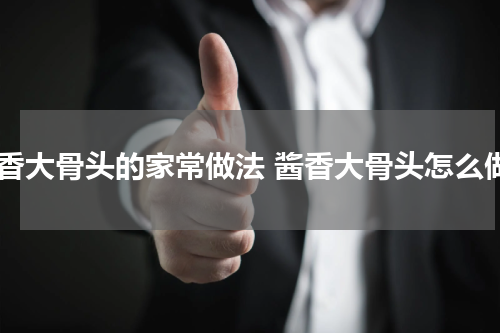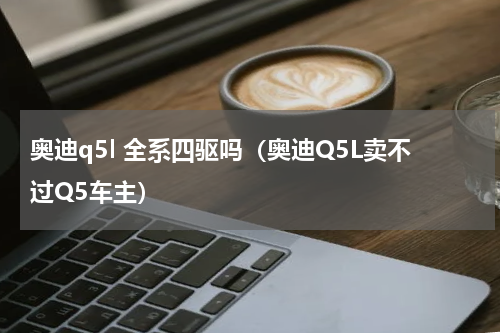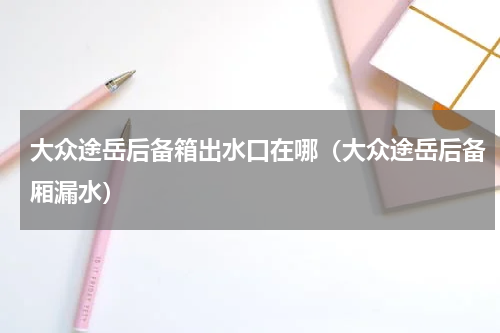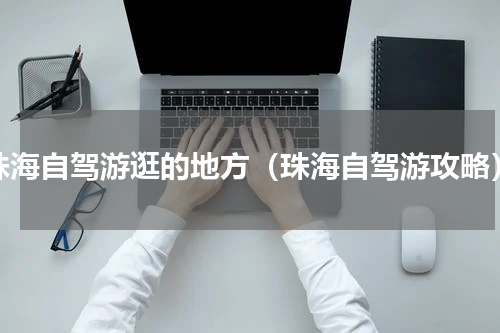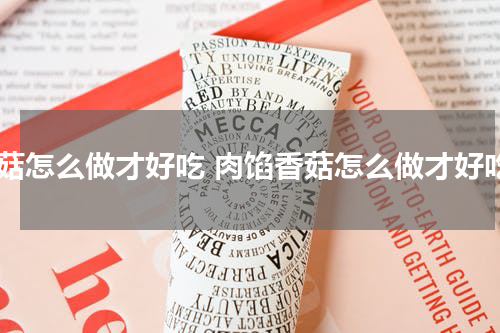莫言被网友谩骂和攻击,竟然已长达10年,可能莫言的余生,都要继续承受偏激网友的谩骂和攻击。但却有爆料称在莫言未获奖前,张一一就已经向诺奖评委索要该奖项,称自己的作品完全符合诺奖评奖标准,可以有资格代表13亿中国人接受诺奖。索要没得到瑞典文学院回应后,张一一又对外宣称,自己将终身不再参加诺奖评选,誓要与诺奖划清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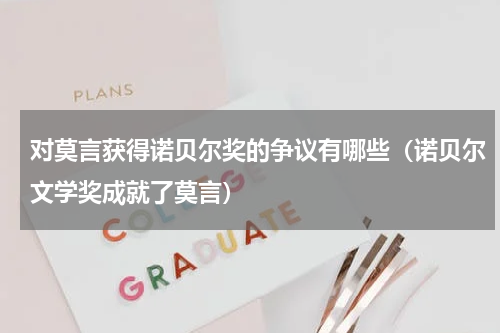
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争议有哪些?现在网上一提到莫言,就会出现两种声音,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争议有哪些?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争议有哪些
现在网上一提到莫言,就会出现两种声音。
一种是称赞莫言敢说真话,是实事求是的伟大作家,表示他把过去的苦难只写了六七成、没完全表达出来。
而另一种则是对莫言进行批判,说他丑化和抹黑了国人,说他的写作就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胃口,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等等。
无独有偶,现在只要是刷到写莫言的文章,底下的评论大多都是谩骂和诋毁的
莫言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理应殊荣加身。
然而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他没能迎来国内应有的鲜花和掌声,反而是被批判、攻击、诋毁和谩骂。
这些声音上来自同行的部分知名作家,下来自普通网友。
甚至有的人压根没有读过莫言的作品,就直接表态,说“我没读过莫言的作品,但我知道他获诺奖与作品无关。”
莫言被网友谩骂和攻击,竟然已长达10年,可能莫言的余生,都要继续承受偏激网友的谩骂和攻击。
有人说中国网友是比较健忘的,一桩热点事件出来,大家骂骂咧咧了一阵,等到新的热点事件出来,大家就会把上一桩事件给忘干净了。
但令人讶异的是,网友们对莫言的惦记,竟然是如此持久,一点都不像健忘的样子。
莫言的遭遇折射出了什么呢?
一、不排除文人相轻、同行相妒
文人相轻同行相妒自古有之,即便是那些作品流传至今的唐代大诗人们,其实某些诗人之间也是互相看不起的,一个认为比一个水准高。
在现代文坛作家们自然也没能逃开这个行业陋习,大家表面上都是斯斯文文的文化人,实际上骨子里也和其他领域的人一样,存在着傲慢和偏见,若非崇拜,那便是相轻和相妒。
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是含金量最高的国际性文学奖项,这是文学界的共识,在文学界它具有最高的社会影响力。
虽然部分中国作家嘴上说着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神话,但其实内心里还是蠢蠢欲动的,毕竟全世界一年只颁给一个作家。
从历史沿革来看,中国文学的繁荣始于先秦时期,流传至今的《诗经》,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文学艺术审美。
之后是鼎盛的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以及近代的五四文学,无不闪烁着灿烂的文学光辉。然而一路有着灿烂文学脉络可寻可考的国度,却对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长达百年,这一点令中国作家很不理解。
所以尽管我们有自己的文学自信,认为中国文学之所以难以走出国际,主要是受限于翻译问题,但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对其他国家作家的偏爱,中国作家还是难免忿忿不平。
对诺贝尔文学奖抱平常心态度、甚至质疑其权威性的作家是有的,但绝不是大部分作家。
为什么呢?因为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具有“最高社会影响力”这一性质,它还具有另一个性质:“最高市场影响力”。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仅是拿到一笔可观的奖金,以及顶着桂冠的那个名头,而是意味着获奖后你还可以靠这个名头让你的书有可观的销量,这才是纯文学作家趋之若鹜的地方。
纯文学想畅销很难,但你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不用说,在获奖的热度期,你的书一定会畅销。
2012年10月莫言获诺贝尔文学的时候,他领到的奖金折合人民币是722万,当时还被嘲这个奖金在北京根本买不了房。
陈光标还扬言要赠送莫言一套北京黄金地段的别墅,任由莫言挑选。在那样的语境下,怎么看都是暗含贬损的意味。
这两种声音间接性贬低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含金量,也折射出了表面光鲜的作家在物质现实面前的劣势,不可谓不悲哀!
不可否认莫言被嘲得不无道理,722万奖金在北京和深圳等一线城市,的确是买不了房。但是722万已经让90%的纯文学作家望尘莫及。
更重要的是,莫言获奖所带来的效益不仅仅是这722万奖金,还有他的作品销量。当年有媒体报道,在获诺奖热度期,莫言的书籍销量猛增199倍,码洋达3.5亿。
获诺奖的这个长尾效应,才是纯文学作家们所趋之若鹜并且为之眼红的。
莫言刚被宣布获诺奖的时候,和韩寒、郭敬明、唐家三少并称“新四大才子”的青年作家张一一,声称莫言获奖是因为贿赂了诺奖评委。
但却有爆料称在莫言未获奖前,张一一就已经向诺奖评委索要该奖项,称自己的作品完全符合诺奖评奖标准,可以有资格代表13亿中国人接受诺奖。
索要没得到瑞典文学院回应后,张一一又对外宣称,自己将终身不再参加诺奖评选,誓要与诺奖划清界限。
然而莫言获诺奖后,张一一除了炮轰莫言,又再次喊话诺奖评委,称诺奖更应该颁给张一一这样的青年才俊,诺奖情结与同行相妒的“葡萄酸心理”可见一斑。
二、难以接受魔幻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也是莫言的作品让读者望而生畏的因素之一。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是拉丁美洲的舶来品,对于中国这个在日常行为上比较中规中矩的民族来说,大部分人还是难以接受这种文学流派的,感觉晦涩难懂,甚至觉得行文奇怪,让人不适。
虽然也有人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并非舶来品,是中国古而有之,如《山海经》、《神异经》、《搜神记》、《聊斋志异》、《西游记》等,就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的源头,但这些作品我们通常还是称为神话故事、神话小说,而魔幻现实主义皆公认为拉丁美洲的文学产物。
魔幻现实主义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行文夸张,比如魔幻现实主义之父马尔克斯,在其鸿篇巨著《百年孤独》里就有多处行文十分夸张的描述——
比如写一个邻居被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用长矛投刺咽喉致死后,死者经常到他们的院子里溜达,到处找芦草塞住咽喉上的空洞。
又比如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有10个同父异母的儿子,这10个儿子都有个共同而奇特的地方,他们额头上都长着一个灰色的十字标志,后来上校的敌人就依靠这个标志,把上校这10个散落在各地的儿子给一一处决掉。
像这种事情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里,它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存在,并且让作品显得更加深刻。
莫言在《丰乳肥臀》里塑造苦难母亲形象的时候,为了让作品显得更加深刻,于是进行了夸张式的描述,但招来了同行和读者的批判,毕竟母亲于我们而言是神圣的,莫言的夸张式描述涉嫌亵渎母性的光辉。
不过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女性的社会地位。现实中的女性为了要儿子,可能没有莫言写得那么夸张,但是至今还有些重男轻女的地方,丈夫和上辈为了要儿子,就逼女方使劲生。
只要前面生的是女儿,那么不管你是生过了七个还是八个,你都要给我继续生,直到生出儿子为止。只要生不出儿子,女方在婆家就抬不起头挺不直腰,这样的事情到了今天依然存在,说明了什么?
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是魔幻的,但内核是基于现实之上,在行文上可以进行夸张、超越常理的处理,从而达到让人印象深刻、难忘的效果。
但并非每个读者都能接受这样的创作手法,这也是莫言的作品令人生畏和误解的因素之一。
还有一方面,莫言的作品在语言上毫无节制,他的写作语言也通常是粗暴啰嗦的,是一种泥沙俱下的表达,作者在表达上是感到淋漓尽致的舒畅了,但在读者看来这样的泥沙俱下的语言却是失去美感的。
我完整读过莫言的作品有《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生死疲劳》《红树林》《白狗千秋架》,只读过部分的作品有《丰乳肥臀》《蛙》《红蝗》《怀抱鲜花的女人》等。
我觉得莫言在构建和行文上最美的作品是《红高粱》,主题积极向上、叙述方式新颖、意象丰沛、人物立体饱满、语言恣意汪洋又有美感,整部作品透着一股原始而坚韧的生命力!读《红高粱》真的是一种享受!
但其他作品在语言叙述上的粗暴啰嗦,常常使我望而生畏!
我们说了,我们中华民族在思想和行为上,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民族,欣赏文学、艺术作品,大部分人喜欢的是含蓄、有美感的表达,对粗暴粗俗式的表达是敬而远之的。
既然敬而远之,自然没有耐心去理解作家到底在表达的是什么,只要看到在表述上有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就容易被断章取义地进行解读。
三、强烈的祖国归属感
除了上述,莫言被批判被谩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众强烈的祖国归属感所引发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新中国成立前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崛起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而且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国民幸福指数大大提升。
随着2017年7月及2018年2月,以也门撤侨事件改编的电影《战狼2》和《红海行动》分别上映后,彻底点燃了民众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之前或许大家都是含蓄地表达对祖国的爱,但《战狼2》和《红海行动》的上映,民众的爱国热情再也藏不住了,全民通过对电影的解读,表达着自己的爱国热情。
人们也通过对电影的解读,向每一个中国公民普及了这样一个常识:假如中国公民在海外身限危险或遭受不公,可以凭中国护照、国旗和国歌寻求帮助和庇护,身后的祖国就是我们强大的后盾。
2019年12月,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中国是第一个以最快速度控制住疫情的国家,也是唯一将疫情控制得最好的国家。因此中国再次让世界刮目相看。
要知道我国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之广,人口达14亿之多,在疫情突然爆发的情况下,居然能做到世界最好,这成绩是有多傲然!
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不少国家失控,失控的原因,有国家政府层面的不作为,也有医疗条件的短缺,不少外国民众及被困在海外的华人,对中国的安全环境羡慕到无以复加,因此也再一次加深国人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强烈的祖国归属感,令国人对维护祖国形象的信念也愈发强烈。因此我们看不得我们的国家社会被抹黑,看不得国人被丑化。
莫言的文学作品,描述的主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和事,那时候中国还没进入改革开放期。
那时候的中国,还是一个经历了将近300年的清朝腐朽统治及将近40年的民国战乱后,刚刚成立了10来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还存在着很多历史进程中的社会问题。
那些社会问题,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一定会存在的,因为那时候的中国,还在摸索着前进,没有经验,也没有参照物。
由于我们是一个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之路,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和借鉴。
历史进程中的社会问题虽然难以避免,但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作家眼中,这些问题也是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的,不是说难以避免我们就可以不去正视和矫正它。
因此对于如莫言的上一辈老作家而言,当他们去书写那个时代,就避免不了会去反映、正视和反思那些社会问题。
然而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的感召下,部分民众容易将文艺家揭露和反思社会问题,定义为抹黑或者丑化国家民族,比如前段时间电影《隐入尘烟》引发的争议,尤其是在国际公开场合发表或演讲,更容易被误解,产生歧义,认为是给西方敌对势力递刀子。
若要论及“抹黑和丑化”国家民族,恐怕魔幻现实主义之父马尔克斯,比莫言更具这一“罪名”。马尔克斯凭借其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获得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是被认为迄今唯一没有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以夸张和暗黑的手法,描写了马孔多镇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百年兴衰,以反映拉丁美洲的历史图景和社会现实。
在这部巨著里,这个国家多年内战,但政府军和反政府军却根本不知道为何而战。而布恩迪亚家族除了缺少沟通、互相猜忌和怨恨、偏执的狂热、各自守着内心的阴暗度日、还有严重的乱伦史。
而国家政府层面,对待老百姓不是欺骗就是镇压,而且还是帮美国企业对老百姓进行的欺骗和镇压、甚至对工人进行大屠杀(见《百年孤独》工业暴乱篇)。
在《百年孤独》里,这是一个愚昧落后、远离文明、积弱积贫、内战不断、重复着历史悲剧的国家和民族,最后被一阵飓风从大地上抹去。
这部著作怎么看都是压抑暗黑的,让读者陷入无法自拔的孤独与绝望的情绪深渊。但是奇怪的是,并没有读者反映说是作者抹黑和丑化拉丁美洲,反而都说是这是一部反映和反思历史社会现实的深刻作品,值得全人类阅读,堪称伟大。
所以我们认为,爱国是要爱的,大家爱国情绪高涨是好事,但历史我们也必须正视。假如历史问题你不写我也不写,那么时间久了,谁还知道我们有过那样一段历史呢?
正视历史不是可耻,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前进,不要重蹈覆辙,让悲剧重演。
不敢正视历史,其实是讳疾忌医,大到国家社会,小到家庭个人,我们都应该正视并反思曾经的错误和悲剧,从而更好地前行,这不是好事情吗?
四、读不了主题沉重的文学
还有另一个原因是,现在的人都读不了主题沉重的文学了,读了几页感觉堵心,便放弃了,大家觉得阅读就是为了愉悦身心的,生活压力本来就大,不想再读沉重的文字,增加心灵负担。
2011年我写了一部以打工妹为题材的主题沉重的小说,是一部反思的悲剧性作品。小说在某平台签约上线后,反响很好,好评率达97%。
大多数读者表示写得很真实,让他们仿佛又经历了一遍曾经的青春岁月,读完让人掩卷沉思,有一定的收获。
但同时也有部分读者反映,悲剧的结尾使得作品显得更加深刻,可让人难以接受这个悲剧的事实。他们希望我以后能多写温暖向上、给人以希望和勇气的作品。这不得不让我对未来的创作有了新的思考。
是的,我们的读者已经变了,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作家还没有变,尤其是老一辈的作家,他们坚持我手写我心的初衷,可读者却对他们望而生畏,故此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八零后九零后的作家们,这两代的作家作者,因为看重市场,所以比较在意读者的需求,针对年轻读者再读不了主题沉重的文学现状,因此大量的轻文学和治愈系的文学作品产生了。
到后来,满书轻松诙谐、爽点遍布的被冠以“小白文”的网络小说更是大行其道。从中反映出读者结构的重大变化,读者的喜好变得让老一辈作家无所适从。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莫言及其作品为何让人望而生畏。
读者结构的重大变化,和作家一味为迎合市场而不断降低创作门槛,也不得不令我们感到担忧,现在更年轻的一代,几乎没人愿意去写严肃文学了,难道有一天当有人在国际上谈及我们中国文学,就只能谈轻文学和网络文学了吗?
结语:
在莫言获诺奖之前,无论我们承不承认,中国作家们的诺奖情结都是很重的,所以不管怎么说,于文学领域而言,莫言都是为中国作家圆了诺奖梦。
现在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崛起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在西方列强的环伺之下,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战战兢兢,而是挺直了腰杆,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现在我们既有经济自信、科技自信、文化自信,也有文学自信,所以对于诺奖,我们无需过于拔高而妄自菲薄,但也无需以意识形态去过于揣测,那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
对于莫言也一样,莫言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一个完人,所以我们对待莫言及其作品,既无需一味盲目崇拜,但也不应全部否决!
我们可以弃读他的作品,也可以认为他的作品还达不到理想状态的作品,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莫言的小说叙述角度是新颖而特别的,如《红高粱》是以一个晚辈的全知视角进行叙述,《红树林》是以主人公的影子的视角进行叙述,《生死疲劳》则是以动物的视角进行叙述的。
同时莫言的叙述人称又是自如切换的,比如同一本书里,有些地方是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有些地方又切换到第二人称进行叙述。
莫言的小说结构是千变万化的,有用章回体结构的,如《檀香刑》;有用书信体 话剧结构的,如《蛙》;也有用佛教世界观的六道轮回结构,如《生死疲劳》。
莫言的小说创作,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叙述方式和结构形式,这是值得同辈尤其是后辈作家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上述仅代表我个人的感受,至于贡献之外或者说是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