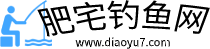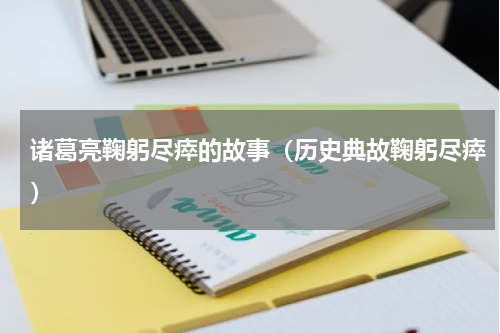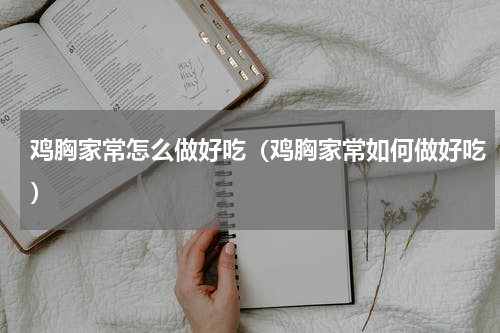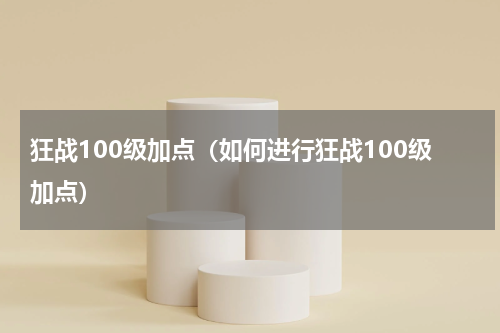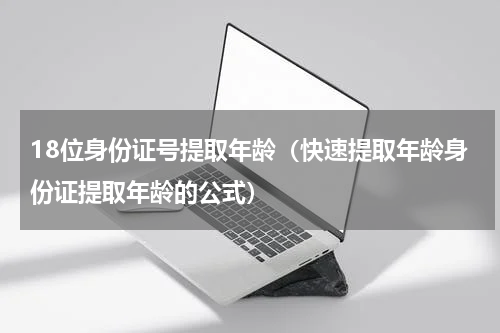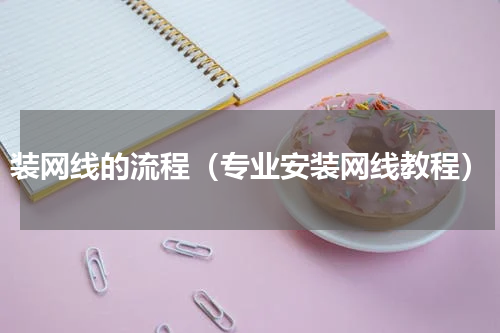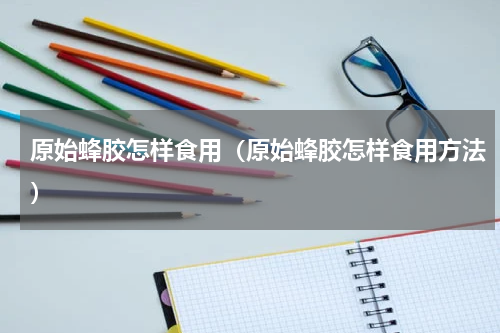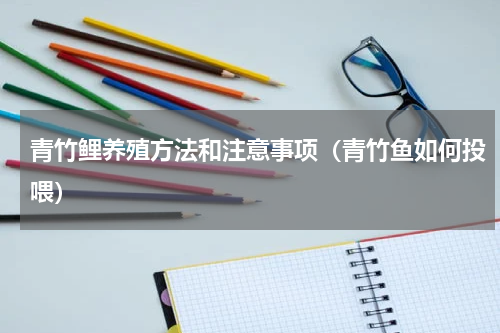“绿色”隐喻着危险的出轨信号。王娇蕊以国人的审美来看,“绿色”是一个矛盾的色彩。绿色被认为是低贱的色彩。绿色地位低下,实际上和当时的染色技术有很大关系。但也有例外,比如伊斯兰国家。这两种强烈的反差带来的小丑形象感通过主人公的服饰有所展现:灰衣上饰及绿色的绶带。在莫里哀的作品里,大多数滑稽可笑的角色都是身穿绿色服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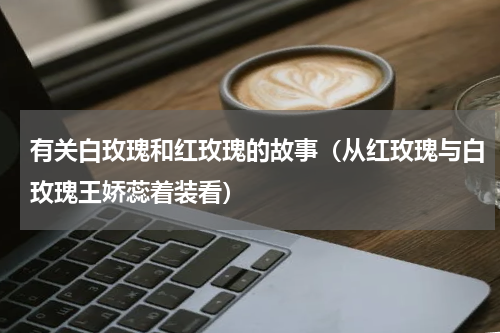
在看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时,王娇蕊出场的服饰很是吸引我。
有一幕讲刚巧佟振保回来,听到王娇蕊在和异性打电话,约他到家里来喝茶。佟振保走到阳台上,王娇蕊也迎了出来。
佟振保看了她一眼,她穿着的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
还有一幕讲半夜电话响了很久,佟振保去接,看到王娇蕊:
换上一套睡衣,是南洋华侨家常穿的沙龙布制的袄裤,那沙龙布上印的花,黑压压的也不知道是龙蛇还是草木,牵丝攀藤,乌金里面绽出橘绿。
在为数不多的描述王娇蕊的着装里,“绿色”这个色彩词就出现了两次。张爱玲重笔墨来描写王娇蕊的服饰,是有深意的。这两幕都出现在两人互相试探和调情的阶段。“绿色”隐喻着危险的出轨信号。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都染绿了,佟振保逃不掉的。
王娇蕊
以国人的审美来看,“绿色”是一个矛盾的色彩。它是自然之色,健康之色,生命之色。但同时它也是欲望的象征。大概很少有人会戴“绿帽子”出门。
所以就有了一个问题: “绿帽子”是如何成为被出轨的代名词的呢?绿色这一意象的象征意义是怎么演变的?
从古至今,我们赋予色彩很多的情感。红色代表正义,也可以是火辣性感;蓝色代表纯净,也可以是忧郁;绿色是希望之色,也可以是欲望之色。
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帕斯图罗在《色彩列传·绿色》中指出:
在艺术创作中,色彩的符号象征功能比审美功能要重要得多。每种色彩都与善恶、情感、年龄、社会阶层、伦理观念、道德准则等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每种色彩价值的背后是一整套的社会规范。
古时色彩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绿色被认为是低贱的色彩。唐初史学家颜师古在注解《汉书·东方朔传》时写道“绿帻,贱人之服也”。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也有“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的说法。
像古时候为人诟病的“碧绿青”着装,在《元典章》记载中仅限于娼妓和乐人所穿。
绿色地位低下,实际上和当时的染色技术有很大关系。绿色的萃取通过植物染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染出来的绿色很不稳定,容易褪色。一般只有等级比较低的人才会穿。
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一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被贬后的诗人只有穿“青衫”的资格。
青衫这种颜色肯定不是纯正的绿色。因为无论是在唐朝还是欧洲的中世纪,纯正绿色的萃取是非常难的。
在欧洲,天然的绿色才是庄严高贵的,它代表上帝的造物。人工制造出来的绿色,属于次等色。一是因为它们不稳定易褪色,二是在当时的欧洲,通过黄蓝两种颜色混合出来的颜色被认为是“不纯正”的。
看米歇尔·帕斯图罗的《色彩列传·绿色》会发现,绿色在欧洲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可以说这是一种一出生就被列为“低贱”的颜色。
旧石器时代的所有绘画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绿色系的任何色彩。而在古希腊语,有关绿色这个色彩的词汇也很贫乏。
在米歇尔·帕斯图罗看来,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环境中,一种色彩没有被命名,或者很少被提及,并不是因为人们看不见它,而是因为它在生产活动、社会交往、宗教仪式、符号象征、文艺作品等方面的地位很低。
后来随着社会规范的发展,绿色经历了受人重视和被人贬低的反复历史。在很多国家,绿色有正面意义,也有反面意义。但也有例外,比如伊斯兰国家。在伊斯兰世界,绿色总是积极正面的。这些国家的国旗上几乎都有绿色元素的存在。
在文学大师中,莫里哀是一个喜欢“绿色”服饰来展现角色的知名戏剧家。1666年,莫里哀的《愤世者》在巴黎皇家宫殿剧场首演。里面的主人公阿尔塞斯特表面上向上流社会宣战,反对妥协、虚伪的礼仪和朝三暮四的爱情。背地里他却经常造访肤浅任性的贵妇赛丽麦的沙龙,大献殷勤。这两种强烈的反差带来的小丑形象感通过主人公的服饰有所展现:灰衣上饰及绿色的绶带。
在莫里哀的作品里,大多数滑稽可笑的角色都是身穿绿色服饰。比如《贵人迷》中一心想做贵族的资产者茹尔丹先生。
茹尔丹先生:没事。我是想试试你们听见我喊了没有。(向两位教师)我这两个听差穿的制服,你们觉得怎么样?
舞蹈教师: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好看的啦。
茹尔丹先生:(把睡衣掀开,露出红绒短裤、绿绒短外褂)这一身便服是早晨活动身体时穿的。
比如还有他的《无病呻吟》里坚持把女儿嫁给托马斯·迪亚弗医生的阿拉冈,《屈打行医》里被妻子欺骗,又被求医者暴揍一顿的斯加纳莱。
绿色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非常广泛。本文只是拙劣地做了简要的阐释,是非常浅显的。欢迎补充,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