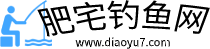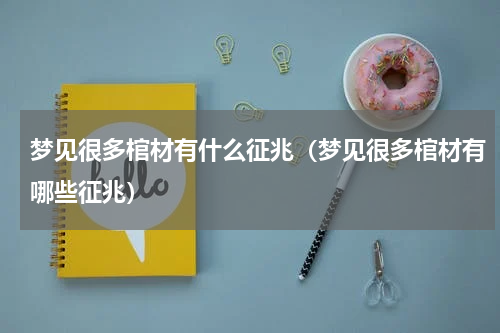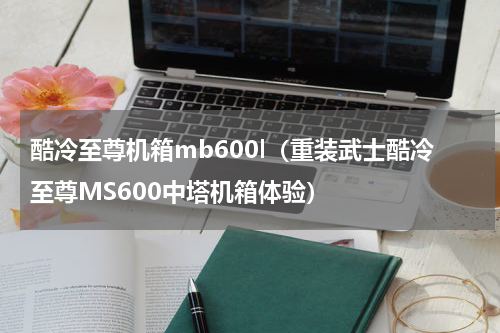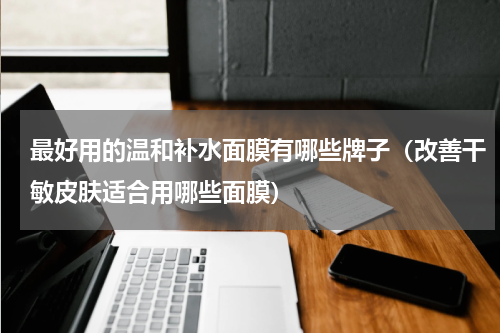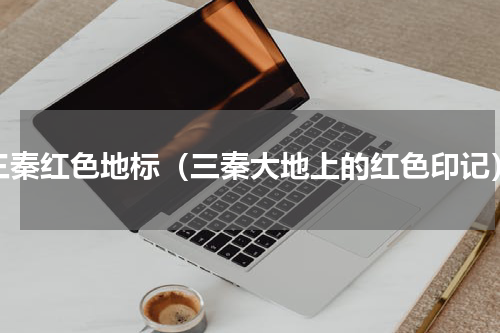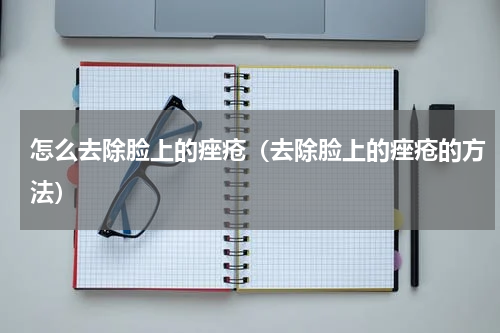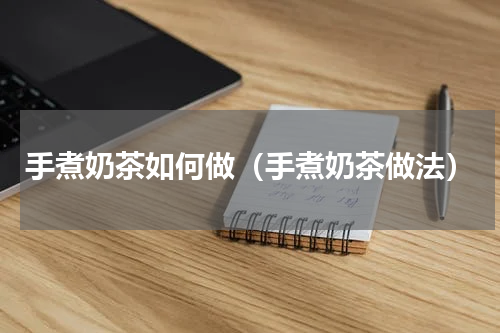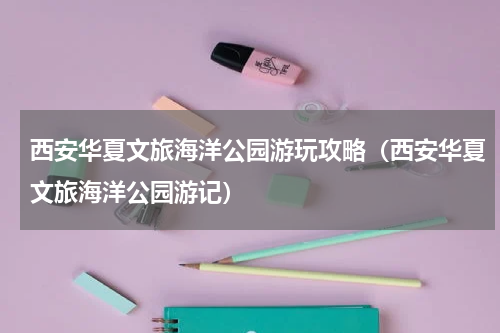过去强调保护国家财产就是保护国家利益,这不对。如果国家财产被无故侵犯,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侵犯者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当然不好。这些内容不是民法应该规定的,世界各国也没有一个在民法典里规定刑事责任。法律明确规定,对私人财产进行限制和剥夺必须有法律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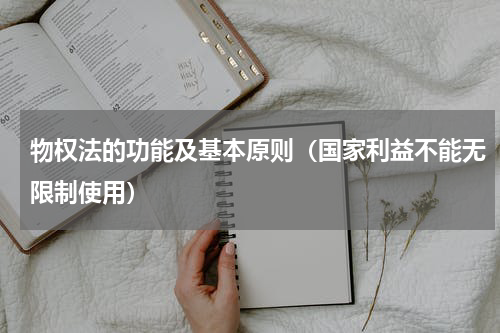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原校长,《物权法》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
王轶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陈华彬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教授、法学博士、《物权法》起草者
就物权法三审草案,著名法学家江平等接受了本报的采访,访谈围绕国家财产的保护、野蛮拆迁、拾遗物补偿金争议、业主维权,以及未来民法典的起草等热点话题展开。
保护国家财产入法不等于轻视私产
物权属于私域范畴,它天生与公共领域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时代变迁使得这种距离也在缩短。这次新的物权法草案强调“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破坏国家、集体和私人的财产”,就体现了这一点。
新京报:国家财产所有权是否属于物权法保护的对象?
江平: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而动产和不动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家财产,如果涉及到国家财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财产也就是国家利益。物权法要对财产进行平等保护,既保护私人财产,也保护国家财产;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过去强调保护国家财产就是保护国家利益,这不对。但现在也不能够只强调保护私人财产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国家利益有一定道理。
王轶:物权首先是所有权,那么国家所有权是不是就是国家利益这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如果强调说国家所有权就是国家利益,保护国家所有权就是保护国家利益,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对国家所有权设置跟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不同的保护规则,这个是违反民法上的平等原则,也是违反物权法对于所有物权一起保护这样一个精神。
新京报:既然如此,在物权法领域,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又是什么关系?
江平:不能笼统地、无限制地使用国家利益,把国家利益跟私人财产、私人利益相对立,讲国家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私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这不对。当“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时候,可以征收私人财产,而不是说当“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可以征收私人财产。这个用词很重要,因为国家利益有时并不明确,所以还是避免使用“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征收私人财产”这样的说法。
王轶:我们今天所有的国家利益应该作一个严格的限定: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这种国家利益当它在和一个民事主体的私人利益处于冲突时,可以把私人利益放在靠后的位置甚至放弃私人利益。
新京报:在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财产方面,物权法三议稿与以往有哪些变化?怎么评价这些变化?
江平:三议稿增加了关于保护国家财产利益和集体企业利益的内容。我想这有它进步的意义,也可能会造成理解上的分歧。积极的意义无非是我们确实应该防止国有资产被非法侵吞或流失,这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国家财产被无故侵犯,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侵犯者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当然不好。
但也不要理解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就优先于或者高于私人利益,或者它们是不同样、不平等的。
新京报:私法传统悠久的国家怎么规定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的?
江平:西方国家没有所谓集体所有这个概念,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但财产本身分为私人所有和国家所有,这是各国都有的。但在法律中区别保护,这可能是中国特有的。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都没有对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进行区别保护。但也要看到,不少国家和地区专门立法保护国有财产,比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有专门的国有财产法。
新京报:对国有资产保护进行专门立法,是基于什么考虑?
江平:因为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有个很大的不同:私人财产的归属和支配很明确,国家财产权属比较明确,但支配问题比较复杂。首先,谁有权代表国家来行使权利?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权利由国会来行使?政府来行使?
还是由政府某个部门(如财政部)来行使?所以专门立法保护国有资产是可以的。许多国家也是采取了这个办法。
行政、刑事责任入法有待商榷
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物权法草案在这方面做了不小的尝试:草案第四十三条规定,“侵害物权,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京报:在民事法律中规定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该怎么看待?
江平:三议稿规定的这些内容,是值得商榷的。这些内容不是民法应该规定的,世界各国也没有一个在民法典里规定刑事责任。我们正在制定国有资产法,有些问题可以在国有资产法里规定,所以我不赞成把刑事责任也写进民法典。同理,将行政手段写进物权法也容易产生副作用,物权法不应该突出这种色彩,以免造成国家财产、集体财产不同于私人财产,应有特殊保护这样的印象。
新京报:物权法三议稿为什么规定国家财产的有关内容以及行政和刑事责任条款?
江平:有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原因。意识形态的原因恐怕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国家财产、全民财产和集体财产以及公有制,似乎公有制决定了国家财产要高于私人财产,公有制是经济基础,宪法里边都有这些类似内容。
人们往往认为,不注意这个问题会不会改变我们国家性质。现实的原因就在于,通常私人财产保护有确定主体,不是随便容易被别人侵犯;但国家财产现在确实是很容易被侵犯的,尤其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国有财产流失,所以人们基于对现实的忧虑,提出这些建议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有些写法还是需要再斟酌。
新京报:您在不同场合谈到要从制度上抑制公权力滥用,前不久您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也谈到要警惕国家公权力侵犯公民私权利。前面提到的物权法三议稿有关规定,是不是容易导致国家公权力在物权领域滥用的可能?
江平: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预或者侵犯,这是现在的主要危险,我一直这样说。
私权利跟私权利之间的侵犯,当事人到法院去,法院只要能公平解决就好办。公权力和公权力之间发生冲突也好办,我们现在终究有党的统一领导,有什么纠纷,党的内部系统也许就能解决。最大的问题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这主要涉及到私权利被侵犯的几种途径,现在主要在于征收征用。法律明确规定,对私人财产进行限制和剥夺必须有法律依据。
没收有没收的依据,财产保全扣押有保全和扣押的依据,这些问题还比较好说。难点恰就在于,如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公民该怎么办?比如城市要建设,国家经济要发展,因此征农民土地,动老百姓房子,这一部分现在矛盾冲突比较大。老百姓并不是因为其自身违法行为导致财产被没收扣押而有意见,而是因为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把公民财产给拿走而有意见,所以在这方面看来,从制度上抑制公权力侵犯公民私权利是最根本的。
新京报: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从法律设计上讲,怎样让公权力和私权利在各自轨道上各行其是?
江平:现实社会中,私权利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的。自由没有绝对,自由有个边界和限度,关键在于确定这个限度和边界在哪里,什么情况下公权力可以介入私权利,什么情况下公权力不能够介入私权利?这个界限要弄清楚。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这个界限也是民法典或者物权法要规定的。物权法规定了征收征用,但现在还是比较简单。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关键是要确定公权力介入的限度。
新京报:怎么评价物权法三议稿对此的划界?
江平:第一,“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没有确切解释,往往可以被滥用。世界各国也都规定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可以征收,但人家是区分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和商业需要的。现在往往将商业需要也理解为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只要城市发展、城市需要,哪怕搞超市、搞各种娱乐经营场所,也被认为是公共利益。这是不对的。
再一个就是如何补偿。现在的写法是“有国家规定的,依照国家规定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要合理补偿”。这话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什么叫国家规定?北京市政府规定是不是国家规定?一级政府的规定是不是国家规定?国家是一个空的东西,如果政府代表国家,那么在不同的具体事务中,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如果是,地方政府到哪一级可以代表国家?县政府做出的规定是不是国家规定?所以这种说法不准确。
第二,如果国家规定错了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启动国家赔偿?如果政府做的规定错误怎么办?公民能不能起诉?不是说国家规定就一定合理,所以对这种规定我很不以为然。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法律中每个用词的含义明确,必须是由法律或者法规来明确。比如,“合理补偿”应该得到明确:市场经济下,所谓“合理”就是合乎市价。再有,“给予安置”这种话很不准确。我是很不同意民法中使用这样的语言。
王轶:立法机关很难确定什么叫妥善,叫合理补偿,政府也不能,它只能设立一些听证程序来听取民意,只能靠法官来确定和判断。